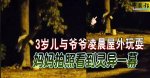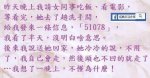2/3
下一頁
蒙古帝國轉折點:阿里不哥手握蒙古中央軍,忽必烈靠什麼逆襲上位

2/3
和他站一塊的,不只是蒙古貴族,還有中原的漢軍、色目軍、契丹舊部、乃至東道諸王中的塔察兒等一票實力人物。別看阿里不哥有中央軍,但兵在北邊,鞭長莫及;忽必烈在中原,地利人和,一樣不缺。
他沒急著回哈拉和林,而是1260年4月,乾脆在開平(今內蒙古正藍旗)自己稱汗,搶了個先機。這是個啥地方?距離和林不遠,又能呼應燕京,是他專門新建的政治基地。再說稱汗不是喊口號,還得有章程。他第一時間發布《即位詔》,明確表示:祖述成吉思汗之法,但要因時制宜,引入中原治理體系。
緊跟著,又發布建元詔,定年號為「中統」。別小看這個操作,「建元」在漢地等於登基大典,是王朝正統的象徵。他這招一下,不光擺明了要稱帝,還要在制度上和阿里不哥「分庭抗禮」。
而阿里不哥這邊呢?雖說是「蒙古嫡長子繼承制」的代表,但到了打仗,才發現真不是騎馬射箭那麼簡單。他缺乏地面控制力,南下道路崎嶇,糧草供給不足。更要命的是,忽必烈還打了一手絕殺:掌控了秦隴地區,切斷了漠北通往關中的糧道。
於是中央軍,成了「中央沒糧」的軍。到了1261年,阿里不哥揮師南下,遭遇昔木土腦兒一戰大敗。那仗打得,不光士兵死傷慘重,更重要的是徹底打碎了他的戰鬥意志和戰略通道。
「從勸酒到勸進」:忽必烈的飯局戰術有多毒?
蒙古大汗的傳位方式一直都不靠譜。沒有立儲制度,沒有明確繼承人,誰搶得快、誰拉得多,誰就是下一個汗王。
所以忽必烈稱汗那天,不是在廟堂,也不是在草原,而是在開平城的一場「飯局」里。說是飯局,其實就是個諸王大會,但這飯局安排得叫一個精巧——坐在主位的是塔察兒,成吉思汗弟弟的孫子,地位擺得明明白白。
這人以前攻宋失敗,被蒙哥訓過,心裡早不舒服。忽必烈也不是糊塗人,在稱汗之前,特意派出了大內智囊廉希憲去「拉關係」,早早和塔察兒談好了「君子協定」:你勸進,我登基。
果不其然,到了現場,塔察兒第一個起身,說自己「願意推戴忽必烈為汗」。別的宗王一看風向全變了,紛紛附和,什麼合丹、阿只吉、忽刺忽兒,全都照著劇本來。這波操作,現代人叫輿論引導+政治排場+順水人情,你要是不同意,顯得你不懂事。
而這背後,正是忽必烈從中原官場學到的一手軟招。他不靠刀子,而是靠策士。他身邊的中原幕僚,不是一般人,有的是舊金朝的文臣、有的是南宋降將,還有契丹、女真、色目人,全都是搞治理的能人。
所以就在稱汗不久後,他立刻開建燕京宣慰司、中書省、十路宣撫司,分管中原大大小小事務。各地的漢族官員開始登台,逐步接手治理。這就意味著:他不只是在爭位,他還在「另起爐灶」,搞一整套政權結構。
反觀阿里不哥,還在走成吉思汗的老路,靠宗王議事、靠草原動員,這在1260年代的蒙古,已經開始「水土不服」了。尤其是當中原開始作為主要財政供給區之後,誰控制中原,誰才能控制帝國的未來。
更離譜的是,忽必烈連法統都沒放過。他在《即位詔》中寫道:「祖述變通,正在今日。」意思很直白,我不是背祖忘本,我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搞現代化。你說你是嫡子,但你沒跟上時代!
所以,阿里不哥不是輸在槍桿子,而是輸在飯局裡,輸在了制度設計上。
「打到沒飯吃」:昔木土腦兒一戰,兄弟情斷了
昔木土腦兒在哪?今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東部,一塊山地地形複雜的地方。這個地方本來名不見經傳,卻因為1261年的那場決戰,被寫進了蒙古帝國的歷史深處。
話說1261年春,阿里不哥看忽必烈稱汗一年還不倒台,終於坐不住了。他調動漠北軍隊,兩路南下,一路打中原、一路走隴右。目的只有一個:打爛忽必烈的後勤線,把汗位拿回來。
但他打錯了算盤。忽必烈早布好局,在陝西一線布下漢軍主力,由汪良臣、廉希憲分路部署,總計3萬精銳部隊,扼守河西走廊和隴東重地。而且,這些兵不是草原騎兵,而是熟悉地形、擅長守城打防禦的中原軍。
阿里不哥的部隊,一入關中,發現啥都缺——補給缺、糧草缺、地形資料缺、百姓支持更缺。戰鬥還沒開打,士氣已經「見底」。
到了昔木土腦兒,雙方展開決戰。阿里不哥的兵前有險阻、後無退路,還沒等擺好陣型,就被守軍用「圍點打援」的策略打得崩盤。最關鍵的是,忽必烈的戰法是混編戰術:騎兵衝鋒、步兵絞殺、弓箭遠擊、火器支援,各種戰術花樣都用上了。
這仗一打,阿里不哥就知道沒救了。昔木土腦兒之敗,是他從戰略攻勢全面轉為防守的拐點。此後他退回和林,一蹶不振。雖然還掙扎了幾年,但連蒙古草原都開始有部族倒向忽必烈。
他沒急著回哈拉和林,而是1260年4月,乾脆在開平(今內蒙古正藍旗)自己稱汗,搶了個先機。這是個啥地方?距離和林不遠,又能呼應燕京,是他專門新建的政治基地。再說稱汗不是喊口號,還得有章程。他第一時間發布《即位詔》,明確表示:祖述成吉思汗之法,但要因時制宜,引入中原治理體系。
緊跟著,又發布建元詔,定年號為「中統」。別小看這個操作,「建元」在漢地等於登基大典,是王朝正統的象徵。他這招一下,不光擺明了要稱帝,還要在制度上和阿里不哥「分庭抗禮」。
而阿里不哥這邊呢?雖說是「蒙古嫡長子繼承制」的代表,但到了打仗,才發現真不是騎馬射箭那麼簡單。他缺乏地面控制力,南下道路崎嶇,糧草供給不足。更要命的是,忽必烈還打了一手絕殺:掌控了秦隴地區,切斷了漠北通往關中的糧道。
於是中央軍,成了「中央沒糧」的軍。到了1261年,阿里不哥揮師南下,遭遇昔木土腦兒一戰大敗。那仗打得,不光士兵死傷慘重,更重要的是徹底打碎了他的戰鬥意志和戰略通道。
「從勸酒到勸進」:忽必烈的飯局戰術有多毒?
蒙古大汗的傳位方式一直都不靠譜。沒有立儲制度,沒有明確繼承人,誰搶得快、誰拉得多,誰就是下一個汗王。
所以忽必烈稱汗那天,不是在廟堂,也不是在草原,而是在開平城的一場「飯局」里。說是飯局,其實就是個諸王大會,但這飯局安排得叫一個精巧——坐在主位的是塔察兒,成吉思汗弟弟的孫子,地位擺得明明白白。
這人以前攻宋失敗,被蒙哥訓過,心裡早不舒服。忽必烈也不是糊塗人,在稱汗之前,特意派出了大內智囊廉希憲去「拉關係」,早早和塔察兒談好了「君子協定」:你勸進,我登基。
果不其然,到了現場,塔察兒第一個起身,說自己「願意推戴忽必烈為汗」。別的宗王一看風向全變了,紛紛附和,什麼合丹、阿只吉、忽刺忽兒,全都照著劇本來。這波操作,現代人叫輿論引導+政治排場+順水人情,你要是不同意,顯得你不懂事。
而這背後,正是忽必烈從中原官場學到的一手軟招。他不靠刀子,而是靠策士。他身邊的中原幕僚,不是一般人,有的是舊金朝的文臣、有的是南宋降將,還有契丹、女真、色目人,全都是搞治理的能人。
所以就在稱汗不久後,他立刻開建燕京宣慰司、中書省、十路宣撫司,分管中原大大小小事務。各地的漢族官員開始登台,逐步接手治理。這就意味著:他不只是在爭位,他還在「另起爐灶」,搞一整套政權結構。
反觀阿里不哥,還在走成吉思汗的老路,靠宗王議事、靠草原動員,這在1260年代的蒙古,已經開始「水土不服」了。尤其是當中原開始作為主要財政供給區之後,誰控制中原,誰才能控制帝國的未來。
更離譜的是,忽必烈連法統都沒放過。他在《即位詔》中寫道:「祖述變通,正在今日。」意思很直白,我不是背祖忘本,我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搞現代化。你說你是嫡子,但你沒跟上時代!
所以,阿里不哥不是輸在槍桿子,而是輸在飯局裡,輸在了制度設計上。
「打到沒飯吃」:昔木土腦兒一戰,兄弟情斷了
昔木土腦兒在哪?今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東部,一塊山地地形複雜的地方。這個地方本來名不見經傳,卻因為1261年的那場決戰,被寫進了蒙古帝國的歷史深處。
話說1261年春,阿里不哥看忽必烈稱汗一年還不倒台,終於坐不住了。他調動漠北軍隊,兩路南下,一路打中原、一路走隴右。目的只有一個:打爛忽必烈的後勤線,把汗位拿回來。
但他打錯了算盤。忽必烈早布好局,在陝西一線布下漢軍主力,由汪良臣、廉希憲分路部署,總計3萬精銳部隊,扼守河西走廊和隴東重地。而且,這些兵不是草原騎兵,而是熟悉地形、擅長守城打防禦的中原軍。
阿里不哥的部隊,一入關中,發現啥都缺——補給缺、糧草缺、地形資料缺、百姓支持更缺。戰鬥還沒開打,士氣已經「見底」。
到了昔木土腦兒,雙方展開決戰。阿里不哥的兵前有險阻、後無退路,還沒等擺好陣型,就被守軍用「圍點打援」的策略打得崩盤。最關鍵的是,忽必烈的戰法是混編戰術:騎兵衝鋒、步兵絞殺、弓箭遠擊、火器支援,各種戰術花樣都用上了。
這仗一打,阿里不哥就知道沒救了。昔木土腦兒之敗,是他從戰略攻勢全面轉為防守的拐點。此後他退回和林,一蹶不振。雖然還掙扎了幾年,但連蒙古草原都開始有部族倒向忽必烈。
 奚芝厚 • 274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274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1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1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51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51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