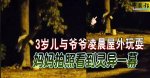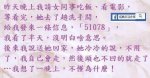3/3
下一頁
1097年冬夜:一個党項人帶三千宋軍,偷了党項人的老巢天都山

3/3
三、死亡行軍:三千將士的冰血征途
十二月初七夜,氣溫驟降至「人馬呼氣成冰」(《西夏書事》)。折可適令士卒「人銜枚,馬裹蹄」,自鎮戎軍(今寧夏固原)悄然出發。
為躲避西夏哨卡,宋軍繞行黃鐸堡(今寧夏海原黃鐸堡鄉)西側無人區。
《宋史·折可適傳》詳載路線:「夜逾沒煙峽,循白草川西行,踐冰渡河者七。」
所謂「河」,實為結冰的清水河支流,冰層薄處需匍匐前進。史載有戰馬陷冰窟,「士卒競以肩扛馬腹而出」。
最致命的是嚴寒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引前線奏報:「軍士手足皸裂,血流至踝,然無一人敢聲。」
為防凍僵,折可適命人每隔半個時辰「互擊其背」,互相捶背來取暖解乏。
至五更時分,部隊抵達天都山東麓的洒水平(今寧夏海原樹台鄉),距目標僅剩二十里。
此時,斥候急報:西夏監軍司駐地嵬名阿埋的千人衛隊正在前方紮營!
四、閃電破襲:黎明前的血色烽煙
折可適面臨抉擇:若攻擊嵬名阿埋,可能驚動天都山守軍;若繞行,則可能錯失戰機。
他當機立斷:「此酋在,天都可得矣!」(《續資治通鑑》)。嵬名阿埋成了折可適的下酒菜。
三千宋軍分三路突襲:左翼千人持強弩封鎖營門,右翼千人繞後斷其歸路,中軍精銳直撲主帳。
《宋史·夏國傳》記載此戰慘烈:「昧爽,鼓譟乘之。夏眾驚潰,相蹈藉死者數百。」
嵬名阿埋正醉酒酣睡,被宋軍生擒,其妻妹勒都通(西夏梁太后侄女)亦遭俘虜。折可適更繳獲西夏調兵銅印、軍械無數。
為防天都山守軍察覺,他令士卒「盡斬俘者,焚其屍」(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),僅留兩名通曉漢話的党項貴族為嚮導。戰爭爭得就是你死我活,難免殘酷!
五、天都烈焰:焚盡西夏百年基業
辰時,宋軍抵天都山南麓。此時大雪稍霽,守軍竟未發現山下異動。《西夏書事》痛陳:「戍卒皆謂大雪封山,宋軍不能至,縱酒為樂。」西夏兵也是該當!
折可適命先鋒百人「衣夏人服,操胡語」(《宋史·折可適傳》),詐稱嵬名阿埋使者入山。待寨門開啟,宋軍突然發難,搶占隘口。
史料記載此役關鍵細節:
一是火攻營區,《續資治通鑑》載「乘風縱火,焚其族帳萬區」;
二是破壞鹽池,《宋會要輯稿》稱「投毒於鹽井,使西夏三月不得採鹽」;
三是搗毀行宮,《西夏書事》哀嘆「南牟宮殿,並庫藏圖籍,皆成焦土」。
西夏守軍倉促應戰,所謂的「鐵鷂子」騎兵在狹窄山道上難以展開,反被宋軍弩手的箭靶子,「射人馬皆洞穿」(《宋史·兵志》)。
激戰至午時,天都山核心區盡陷。折可適見好就收,未貪攻山頂殘堡,攜俘虜、繳獲急速回撤。
六、千里追殺:宋夏鐵騎的生死競速
此時,撤退才是宋軍最大的考驗。
西夏梁太后聞訊震怒,《遼史·西夏外記》載其「發銀牌急使,調左右廂十二監軍司兵追截」。
西夏名將仁多保忠率三萬騎自鳴沙城(今寧夏中寧)馳援,試圖在石門峽(今寧夏海原鄭旗鄉)堵截宋軍。
折可適對此早有預案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詳述其布置:
1. 派五百死士攜帶繳獲的西夏旌旗,沿葫蘆河佯裝主力東進,吸引對方注意力;
2. 真正主力則翻越月亮山,經打拉池(今甘肅白銀平川區)北返;
3. 在石門口預設伏兵,以床子弩封鎖穀道。
十二月十一日,仁多保忠追至石門峽,遭宋軍伏擊,「首尾不能救,棄馬登山者十之三」(《宋史·夏國傳》)。
此戰宋軍又「斬首二千級,獲馬匹五千」,更奪得西夏御賜「龍旗」一面。
當折可適部終於返回平夏城(今寧夏固原黃鐸堡),《續資治通鑑》記載感人一幕:「士卒飢凍,至有墮指者,然所攜俘虜、輜重無失。」
看得出來,宋軍軍紀嚴明,而且士氣高昂。
七、戰後餘波:改變西北格局的十三天
此戰前後共計歷時十三日,折可適部往返六百餘里。
《宋史·哲宗紀》總結戰果:「擒嵬名阿埋、妹勒都通,斬首三千餘級,獲牛羊十萬,焚積聚百萬。」
天都山之戰的一把火,使西夏喪失南疆最重要戰略支點。
次年,宋軍趁勢修築平夏城、靈平寨,徹底控制橫山地區。《西夏書事》哀嘆:「自天都既殘,國中點兵,十去其三。」
而被俘的嵬名阿埋倒是展現出幾分氣節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·卷四百九十三》載,此人被押解汴京後,哲宗親審時竟「抗禮不拜」,最終絕食而死。
其妻妹勒都通,則被賜給宋將種朴為妾。
結語
折可適雪夜破天都,是冷兵器時代後勤、氣象、情報、心理戰的巔峰結合。
千年後回望,那支在暴風雪中沉默行軍的隊伍,仍能讓人感受到戰爭藝術的冷酷與壯美。
誰說宋朝無將?這不就是嗎!古之名將不過如此!
就像《續資治通鑑》編者畢沅的評註:「可適此舉,雖孫臏走大梁未足過也。」
十二月初七夜,氣溫驟降至「人馬呼氣成冰」(《西夏書事》)。折可適令士卒「人銜枚,馬裹蹄」,自鎮戎軍(今寧夏固原)悄然出發。
為躲避西夏哨卡,宋軍繞行黃鐸堡(今寧夏海原黃鐸堡鄉)西側無人區。
《宋史·折可適傳》詳載路線:「夜逾沒煙峽,循白草川西行,踐冰渡河者七。」
所謂「河」,實為結冰的清水河支流,冰層薄處需匍匐前進。史載有戰馬陷冰窟,「士卒競以肩扛馬腹而出」。
最致命的是嚴寒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引前線奏報:「軍士手足皸裂,血流至踝,然無一人敢聲。」
為防凍僵,折可適命人每隔半個時辰「互擊其背」,互相捶背來取暖解乏。
至五更時分,部隊抵達天都山東麓的洒水平(今寧夏海原樹台鄉),距目標僅剩二十里。
此時,斥候急報:西夏監軍司駐地嵬名阿埋的千人衛隊正在前方紮營!
四、閃電破襲:黎明前的血色烽煙
折可適面臨抉擇:若攻擊嵬名阿埋,可能驚動天都山守軍;若繞行,則可能錯失戰機。
他當機立斷:「此酋在,天都可得矣!」(《續資治通鑑》)。嵬名阿埋成了折可適的下酒菜。
三千宋軍分三路突襲:左翼千人持強弩封鎖營門,右翼千人繞後斷其歸路,中軍精銳直撲主帳。
《宋史·夏國傳》記載此戰慘烈:「昧爽,鼓譟乘之。夏眾驚潰,相蹈藉死者數百。」
嵬名阿埋正醉酒酣睡,被宋軍生擒,其妻妹勒都通(西夏梁太后侄女)亦遭俘虜。折可適更繳獲西夏調兵銅印、軍械無數。
為防天都山守軍察覺,他令士卒「盡斬俘者,焚其屍」(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),僅留兩名通曉漢話的党項貴族為嚮導。戰爭爭得就是你死我活,難免殘酷!
五、天都烈焰:焚盡西夏百年基業
辰時,宋軍抵天都山南麓。此時大雪稍霽,守軍竟未發現山下異動。《西夏書事》痛陳:「戍卒皆謂大雪封山,宋軍不能至,縱酒為樂。」西夏兵也是該當!
折可適命先鋒百人「衣夏人服,操胡語」(《宋史·折可適傳》),詐稱嵬名阿埋使者入山。待寨門開啟,宋軍突然發難,搶占隘口。
史料記載此役關鍵細節:
一是火攻營區,《續資治通鑑》載「乘風縱火,焚其族帳萬區」;
二是破壞鹽池,《宋會要輯稿》稱「投毒於鹽井,使西夏三月不得採鹽」;
三是搗毀行宮,《西夏書事》哀嘆「南牟宮殿,並庫藏圖籍,皆成焦土」。
西夏守軍倉促應戰,所謂的「鐵鷂子」騎兵在狹窄山道上難以展開,反被宋軍弩手的箭靶子,「射人馬皆洞穿」(《宋史·兵志》)。
激戰至午時,天都山核心區盡陷。折可適見好就收,未貪攻山頂殘堡,攜俘虜、繳獲急速回撤。
六、千里追殺:宋夏鐵騎的生死競速
此時,撤退才是宋軍最大的考驗。
西夏梁太后聞訊震怒,《遼史·西夏外記》載其「發銀牌急使,調左右廂十二監軍司兵追截」。
西夏名將仁多保忠率三萬騎自鳴沙城(今寧夏中寧)馳援,試圖在石門峽(今寧夏海原鄭旗鄉)堵截宋軍。
折可適對此早有預案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詳述其布置:
1. 派五百死士攜帶繳獲的西夏旌旗,沿葫蘆河佯裝主力東進,吸引對方注意力;
2. 真正主力則翻越月亮山,經打拉池(今甘肅白銀平川區)北返;
3. 在石門口預設伏兵,以床子弩封鎖穀道。
十二月十一日,仁多保忠追至石門峽,遭宋軍伏擊,「首尾不能救,棄馬登山者十之三」(《宋史·夏國傳》)。
此戰宋軍又「斬首二千級,獲馬匹五千」,更奪得西夏御賜「龍旗」一面。
當折可適部終於返回平夏城(今寧夏固原黃鐸堡),《續資治通鑑》記載感人一幕:「士卒飢凍,至有墮指者,然所攜俘虜、輜重無失。」
看得出來,宋軍軍紀嚴明,而且士氣高昂。
七、戰後餘波:改變西北格局的十三天
此戰前後共計歷時十三日,折可適部往返六百餘里。
《宋史·哲宗紀》總結戰果:「擒嵬名阿埋、妹勒都通,斬首三千餘級,獲牛羊十萬,焚積聚百萬。」
天都山之戰的一把火,使西夏喪失南疆最重要戰略支點。
次年,宋軍趁勢修築平夏城、靈平寨,徹底控制橫山地區。《西夏書事》哀嘆:「自天都既殘,國中點兵,十去其三。」
而被俘的嵬名阿埋倒是展現出幾分氣節。《續資治通鑑長編·卷四百九十三》載,此人被押解汴京後,哲宗親審時竟「抗禮不拜」,最終絕食而死。
其妻妹勒都通,則被賜給宋將種朴為妾。
結語
折可適雪夜破天都,是冷兵器時代後勤、氣象、情報、心理戰的巔峰結合。
千年後回望,那支在暴風雪中沉默行軍的隊伍,仍能讓人感受到戰爭藝術的冷酷與壯美。
誰說宋朝無將?這不就是嗎!古之名將不過如此!
就像《續資治通鑑》編者畢沅的評註:「可適此舉,雖孫臏走大梁未足過也。」
 奚芝厚 • 274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274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8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11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11K次觀看 福寶寶 • 51K次觀看
福寶寶 • 51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5K次觀看 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
喬峰傳 • 5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5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
花峰婉 • 3K次觀看 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
奚芝厚 • 3K次觀看 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
呂純弘 • 6K次觀看 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
舒黛葉 • 2K次觀看